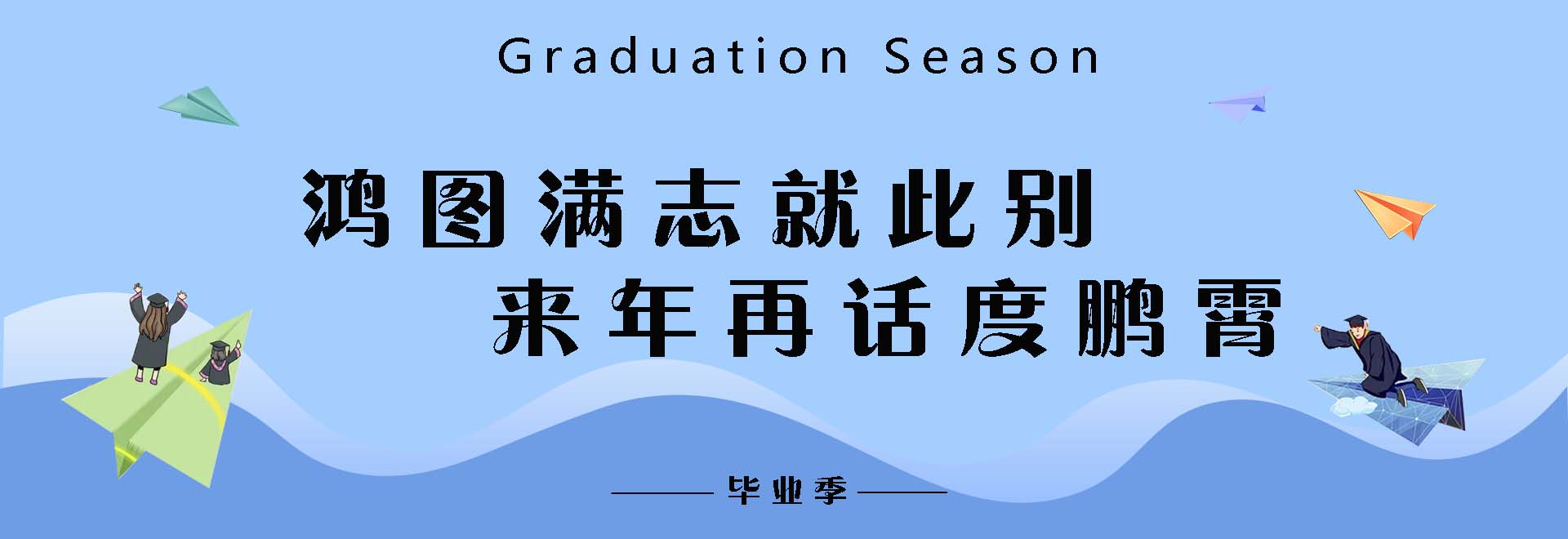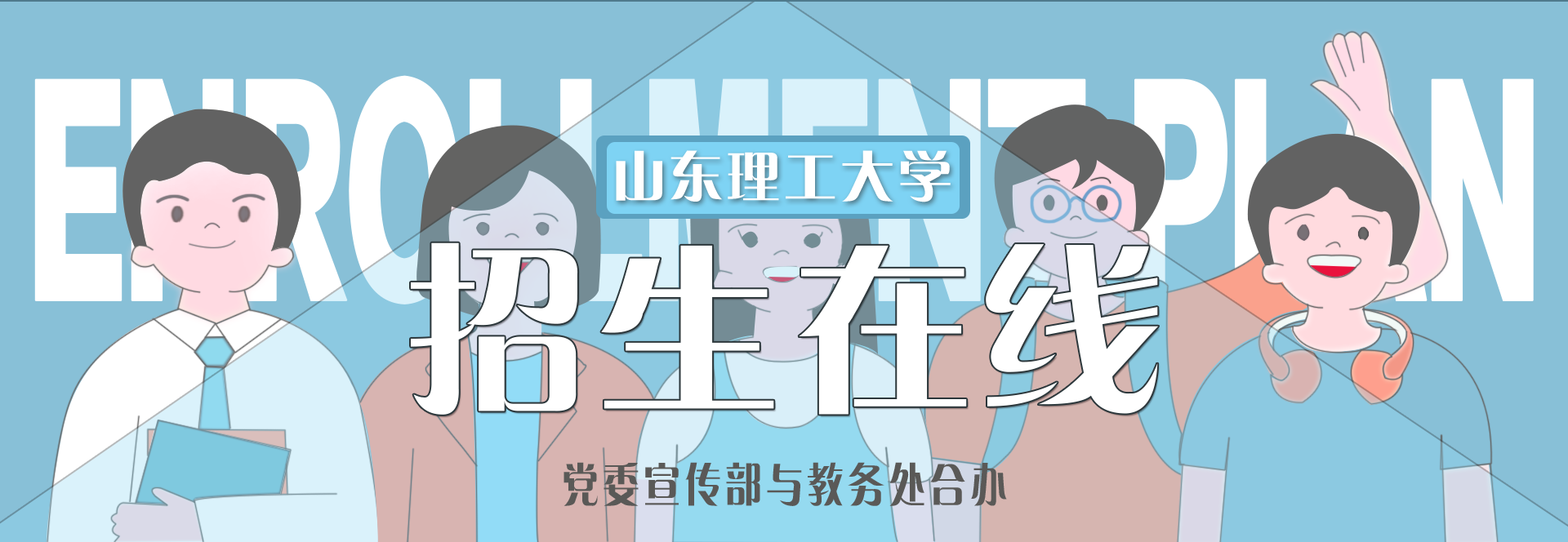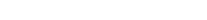踏上故乡的土地,总是有格外的安全感。
每个人的记忆深处,一定都会有一些忘不掉的残存印象,像愈发黄旧的老照片,像常常嘶哑的收音机,常在梦中被想起。想起亲切的人,想到过去的事,是梦醒时的略许惆怅,是遥远的飘着芳香的亲切。
小时候的家乡,有一座不出名的山,因地处县城西侧被大家称作西山,说做是山其实也仅是一座小小的山坡,山坡十分平缓,不一会儿就能爬到山顶。山脚下被政府修葺成一个小型公园,因为纪念孔明,也被称作“诸葛亮公园”,古色古香的仿汉街悠悠扬扬地在山脚蔓延而去。清早,长街上的豆浆油条小店冒着热气,晨练的老人早早地就占据了公园大大小小的角落。旁边有一座高耸的信号铁塔,下面的院子里就是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大楼,院子的大门永远紧紧地关着,写着“闲人免进”。
山上有一块块铺平打好的硬土地和青石块叠成的矮矮壁垒,老人们说那是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,壁垒是战士匍匐在地上托枪用的。我脑中常浮出画面,就像抗战题材的电影里演的那样,年轻的战士冒着弹雨在青石缝中瞄准敌人,义无反顾地抗击着阻拦着敌人前进的步伐。那一个个平地与壁垒便成了年幼时期的我们最大的乐趣,趴在地上写作业,阳光透过浓密的松枝斑驳地洒在身上,或是在青石块上风干山林里找的小蘑菇,只要去西山玩,就一定会去寻找那片小小的壁垒,那是童年的一片乐土。
山虽不是特别高,但站在山顶依旧能将半个小城的风光尽收眼底,也是观看日初看雾飞的绝佳地点。在很早的时候那里还有一座小小的姊妹亭,石子花果做棋子,草茎汁液画棋谱,分外自在。后来亭子没了,留了一座残破的台基,水泥缝中拱出了几棵荆草,去山顶的人依旧不绝。
夏天山里总是格外凉爽,蝉鸣阵阵,厚重的松海在树下洒下了大片的荫凉。丛林深处的某个地方,有泉水从某个不可寻见的古井中流出,潺潺地流淌着,不知在山野的哪里流到尽头而消失不见。夏雨肆虐之后泉水漫涨,混着山土树叶留住的雨水从树根处汇聚静静流出,山道彼时也是水道。
秋冬时节的山,瑟瑟漫漫的一场寒雨淋下,松林也显得萧条一些,颓败的草,带着水珠的干枯木叶,人也少了许些,但少了原来厚密草叶的遮掩,偶尔能看见逃窜其中的山鸡。下过大雪后,漫山遍野就都是青翠顶着白雪,到了那个时候,人就又多了起来。穿上厚厚的棉衣,戴好帽子围巾手套,纷纷出门去寻找雪地里的乐趣。阳光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,闪着刺眼的光芒令人眩晕,但却是永不妥协的美。在没有踪迹的厚厚雪地上张开双臂向后一倒,地面就出来一个“人”字;或是故意呈外八字走路,走过后雪地里就留下了一长串印记,远看像车轮碾过一样。
春天冰雪开始融化的时候,山花春草的生命也开始复苏,迎春花黄黄的一小朵从地面钻出,盛开在未融化完的冰雪之间,晶莹剔透。总能想起当年在雪地里拍下的那些照片,和照片里的人。
那是我记忆里的苍山,记忆里的家乡。如同木心的那首从前慢:
记得早先少年时,大家诚诚恳恳,说一句是一句;清早上火车站,长街黑暗无行人,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;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马邮件都很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……
幼年时的家乡,是渺小的,是落后的,是匮乏的;但那里的水是清澈的,天空是蓝蓝的,那里的人是简单的,那时孩童的自己也是极简单快乐的。